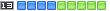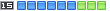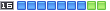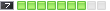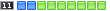文/心之初
少年维特是几岁开始烦恼? 我不知道。十四岁的文革时代的哥哥们,好像除了性欲没有,其他的欲都很全。少年性欲的早期发飙,跟丰富物质营养有关,一月几两猪肉是决对不行。其它的欲,直接就可在革命烈火里燃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就是不守规矩,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道理的千头万绪的“就是一句话”。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大人们全昏,小孩们开怀。
我不到十五,就给一个在我脑底板上成了像的女孩写过“第一信”,因为读了本书,就特想和个女性发展革命友谊。要四十年了,当年的小姐姐,她的孩子都该结婚了,但还在常惦记我,隔着千山万水,跨着阴差阳错。问世间这男友女情为何物,直教人“没完没了”。
上世纪(挺爱写这三个字,跨世纪人曾经了沧海)的一九七零年,全国的城里人都听新中国后最牛的副统帅话,战备疏散到乡下,等原子弹。我和老爸从西安到重庆市郊农村,投奔他的小地主丈母娘。南方的冬天,比起西北,好得实在太多。山青青,水清清,人更清清。那年我是西安初一,转到重庆“三合一”。山城的文革武斗火爆血腥,勇冠神州,复课革命就比其它地方晚。三个年级合一。我怯生生地进了个“人人比我大”的班,坐我后边的,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不过,我那时是“老和尚教的小和尚”,虽说并不把女人看成老虎,但也认作天神。
刚到个新地方,人很乖。凭着聪明和认真,还有比起四川人来讲,标准不少的普通话,两三个月后我就是个学习好能讲话的有点惹人注意的好学生了。就在那段日子,我平生唯一地在百人面前讲过话,跳过舞。孤独让人进步,但后脑勺被不被人多瞅,我不知。
大概是党快过生日的前后,有天我和个哥们儿在校园里玩,到处窜,嘴里哼:我们都是飞行军。不曾注意,就“飞”进一个小天井。一溜翠竹,几盆鲜花,小石板路穿院过,那天下着毛毛雨。平房加小院,住着肯定比万丈高楼好得多。不慎入了私家小院,我心惊惊慌慌,人也急急悄悄,忙忙乱乱,嫩竹梢打着脑袋,猛抬头,一扇窗,眼前一美少女端坐,凝神在写着毛笔大字。我只觉看到一张画,觉着遭了雷击:清澈天空下,绿竹环绕的小院里,一间小书房,坐个写毛笔字的小少女,只能看到她的黛眉和专注。她抬头,好像还冲我一笑。哇,她。我急忙如耗子被猫追,但怀里好像揣上了个兔子(日后,“小兔”会闹腾)。脸没准早已红透半边天,她家没安摄像头?
过了没几天,她在班上教我们唱《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大草原》:“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大草原,翻身的牧民把心中的歌儿唱,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掌大印,紧跟毛主席步步前进”。歌声很悠杨。真不知我怎么到现在还能记得(日后听德德玛的那首《什么中年》,我就眼湿)?就那天,我认真地从三米外看了看她:柳眉下,一对杏眼,鹅蛋小脸,玉腮微红,几分羞涩,几分大方,几分甜甜。十四岁的我,玉树还没临风,看少女,那会得仰首。
那年八月,我回了西安。没有派对,没有大餐,没有握手,没有告别,只有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印在我的小小脑袋。很多年后我一直把那七个月的中学,看作我梦开始的地方。
那会的日子,有劲还多变,谁也不知明天会怎样。白天,全国就像练武场跳舞厅OK房;半夜,据说都在“盼天明”,就像现在当官的白天---都盼夜生活。整天“寒冬腊月盼春风”,按说日子会很长,但对少年我们来说,还是快。“不识愁滋味”好。白天疯玩,夜里暖在被窝里念想念的书。
对我半生震撼最大的一本书,是《斯巴达克斯》,乔奥尼万里写,高植译。每读到斯巴达克斯在和范莱莉亚热烈拥抱着细语着甜蜜着,但当听到战友们的呼唤,斯巴达克斯义无反顾地和同志们走了并死了。我就感动不已。明知力所不及,英雄宁愿在战场上流完最后一滴血地去死,因为义。范莱莉亚,国王的妻或妾,美如天仙,但最可贵的是她的善良和勇敢。书里有句话:女人最重要的是:识别善恶的能力和牺牲精神。
小时侯读书,很容易读进去,恨不得自己就是斯巴达克斯队伍中的一员,最好也能有个 “范莱莉亚”。虽说从重庆揣回的“小兔”在我回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时不时地闹活,但那个又一次读《斯巴达克斯》的深夜里,合上书,闭着眼,据然全是那个下着毛毛雨的小庭院。夜半几更不知道,我用我的全部勇气,给女孩写了第一封信,差不多写了一个星期。
每个一生都有很多第一次,有的让你欣喜若狂,也有的会让你胆战心惊。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吧,我天天都是做了贼的感觉:没跟人家说过一句话,没跟人家对过一次眼,居然就敢想和人家发展“革命友谊”。自己都觉得忘为,太“斯巴达克”了。
每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不管你晚上想什么。生命的蓬勃,在青春欢快的日子里,走道都爱蹦着走。小平二次复出,我们准备直考大学(党的四大前的日子)。就在那些日子里,我收到了 “她”的回信。信封上几行娟秀的字,就已经让我觉着“鱼素”,传来了情,高兴得我跳三步蹦一圈,见个大树都想抱。差不多一年,她才给我回了信。当年,我们纯洁,有种什么,在心里,很神圣?
人心里,真有些“神圣”,心就很幸福。当年的那些“就想”,虽说没有多少变成真的,因为主宰我们每个人的“风向”让我们在大多时侯都只能跟跑,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我们自己是什么喜欢什么喜欢是什么。我们是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大,后来党又不拧我们了。这刚走的三十年,太多“欲说还休”。
十来年前,我完成了我在美国的八年抗战,回国看妈顺便从西安到重庆专程去看和我写了几十年的信但快三十年从没见过的“她”(她老公不愿见我,但不反对她见我)。“岁月”见到“沧桑”,吃两顿饭,听首歌,坐上火车。站台上她那瘦小的身影,一直立到我的视线以外。
5/19/2009(多年前的这天,中国足球输给香港)
[em85][em85][em85][em85][em85][em85][em85][em85][em85][em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