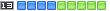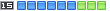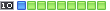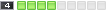//心之初
中国心,很累的。
平常的心,都当成斯人的心。
心存天下,咱的文化里有太多的伦理,忠孝仁义,安身立命,兼济天下,独善其身。道理没错。
“人之初,性本善”。“善”,要“先解放全人类”,最后再解放自己,连有没有最后都不想。“善”,想当大官,发大财,做大事业,搞大名堂,娶小老婆(说过了,哪敢?)。想起卢梭说的:善,就是要“恶”的时侯,心里会有的一种让“恶”戛然而止的力量。
人,挺简单;心,也不复杂。心为身生,身随心动。但人在戏里,就不容易了,不在戏里,又能在哪呢?人生如戏嘛。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这么告诉我们,老师这么教导我们,爹娘这么盼着我们,我们这么鞭策我们。我们会因为“外因”,在心里长年孵着一个蛋。 想当斯人,扛个大任,想得很累,干得更累,忙得心亡,都没工夫想:扛那大任干吗?人心太累,命就短。虽说不好玩,但谁都都还想在人世多呆会,谁知明天有没惊喜。
上大学那会,“我的中国心”是我们最爱唱的歌。每天早上,楼道上都是各种各样的歌吼声喊,不管是走向教室的路上,还是排在买饭的队里,到处都能听到那旋律,把我们中国心弄得跳跳的。好些人(包括我)就是蹲在茅坑上,也在默默“中国心”。我们学校厕所的蹲坑设计很有创意,坑台很高,高过窗台。大概是考虑到人在“马步蹲档”时会觉得无聊,所以让人在“练功”时可以眺望远方。人眼有了东西,就不无聊了,但会情不自禁。明敏的歌里,有几句鏗鏗锵锵叮叮咣咣,“长江”“黄河”,“什么什么,在我心中重千斤”,然后紧接一阵悠扬,悠扬时往往能让人在音律和歌词的帮助下完成“蔬菜水果不太够的日子”里的挺不容易的大事,那一刻我们通常就想把那感觉“大声地告诉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头,中国的“国家状态”还是“精神变物质”,跃迁(很有学问的一个词)平移,保住地球籍。那会不讲“崛起”,实践刚刚出了点真知,十一届三中全会搞定了班子,小平上了美国<时代>封面后指挥我人民解放军把“风采”血染到越南凉山。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全中国的人都在 “一天等于二十年”地去找毛主席领着全国人民“继续革命”掉的好几千个日子。从上到下全民的稀里糊里糊涂,边实践,边出真知,边统一思想,边自主承包,还有很多边边,盼着歪打能有个正着,人性都没恢复,反思也没完成,文艺复兴“小荷刚露尖尖”,人们也没想清仇美
恶善,还在“问苍茫大地”。“有一个老人”从刘司令(司令两眼那会都瞎了,瘫痪了)那里学来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抓,手和爪,两脚离地向前扑,就想把钱拿。人心变猫心。
四年大学,我的中国心在没用的学问里泡过。大学的日子在找日子的日子里很快就过了。大学完的时侯,当年我们“天之骄子“(要知道七七考上个全国前几名的大学的人要怎样在猴子里当个高个)的感觉早都没影了,大家都觉得是糊里糊塗,跟”过把“蚓”“里唱得一样。
“出了大学更糊涂”时,我真不爱念鸟书了,遂改成去教书,教人家念书。自己不爱念的书,教人家念,一样的书,那可就是圣贤书。我讲书的能力比念书强,教得学生比我还会做题,还会得奖。我就很闲,反正没人多给钱。好几年在工科学校教物理,虽说教得很无趣,但也轻轻松松,挣的那点钱,刚够不爱乱花钱的“我一个”。那些年,下了不少围棋,看了不少闲书,写了不少情书。人就是怪,本来“一个人挣钱一个人活”就挺不容易了,还都爱再找个人搭伴,跟“闭花羞月”聊天,给“沉鱼落燕”写信。有个盼头,心就不“空落落”的,但很累。
没结婚,想结婚时我就认为:这婚应该是哑铃式的,就像最稳定的双原子分子。咳,那会的女友今日的太太居然和我还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俩就“西对北,安对京”。人不结婚,也真不知道这俩字是啥意思,那会都二十五六了,还不在乎朝朝暮暮,还一见面就东拉西扯横七竖八。纯洁可真就是力量,不知保尔干柴和冬尼亚烈火是不是坐上一夜,木柴就能炼成钢铁?
八四年到八六年,按理说,国家的什么该“千呼万唤始出来”了,但我好像没觉得那几年有啥大动静。投机倒把那会在中国风起云涌了,胆大的,犯案的,念书不行的,好多人就在那会开始展露头脚了。大学里的人还在批胡耀邦。这城市里的发了的“小人”(小人喻于利)刺激撩拨了“君子”。君子们喻不了“义”了,发现“画的饼”,不顶事。
要搁平常(正常),一个大国领袖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指导人民,人民可能早就叫他“下课”了。可那会,有好多年“灵魂革命”垫底,用肚子想问题的人人就是想当邓政委鼓励的“能先富起来”的“猫”。那时的中国,也没多少老鼠,因为老鼠多不多,取决于粮食多不多。对国家来说,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道理就跟着变。这“变”,奥巴马的口号,如果太剧烈太深刻太频繁太突然太天翻地覆太你死我活,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就老在“打秋千”。人在秋千上,就得跟着变,就得不停地转身不停地变脸不停地勾践不停地梅兰芳。人的心就不停地七上八下不停地十五吊桶不停地打水不停地换油。
“霹雳一声震那天响”,到 “天翻地覆慨而慷”,再到“弹指一挥间”;从“站起”到“打倒四人帮”,再到 “下课胡耀邦”,多少年“茫茫”,“无处化凄凉”。
“而立”,跟催命一样,把人心催得累呀。“走他乡” 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尾有学位的人的时尚。多少中国心,走出了国门,又唱:再过二十年荡个小船。到外国,去唱唱“故乡的云”。
“而立”后,我走了走他乡。到他乡,不用写批判文章。
在美国,我懂了国际歌,“自己脑袋自己扛”,干活累,我的中国心反而不太累。美国只让中国人干活,中国心可以歇着。
不到“河东”到“河西”的周期,我的中国心却出了大故障,差点玩完。心命也在于运动?生命成了“意外”,意外中的生命,挺好玩的。前几年,我常回家看看,不用帮妈妈洗洗碗,妈妈有保姆。我看到许多往日的“熟悉”和这些年的“让人恍然”,我那颗还跳着的中国心老有一种隐隐的痛。我对于我有雨露之恩的大地有份沉沉的爱。爱什么呢?飞过天,走过地,聊过人,我的中国心,想不清了。爱,只是不能忘却吗?
诗的国家没有了诗,情的国家没有了情。只有为身子的文化,为大爷的文化,为身子的产业,为大爷的产业,产业链。到处的按摩,到处的捏脚,到处的浴房,到处的“印象”,到处的OK,到处的饕餮,到处的声嘶,到处的喧闹,到处的道理,到处的虚言。我不会说话了,尽管我觉得自己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说话,看书,成堆的书,找本能读的,和掏金一样。
上帝也许会告诉我们些不明白的东西,而我的中国心里又没有上帝。有些东西,小时侯就该有。
每一次离开,我只能对那片我曾经熟悉的土地道一声万福,对那片我看不清的天空说一声保重。我还会常常回去,因为妈妈还在。
又春节了,我的心挺孤单的。是得爱俩国了,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生活着的国家。爱俩,一心分两半?
1/19/2009
|